伤口在第七天完全结痂,麻痒感取代了疼痛。陈卫国对着那半块破镜子,小心地揭下陈老爹敷的草药糊。痂皮已经变得坚硬,边缘开始微微翘起,底下露出粉色的新皮肤。
愈合情况良好。没有感染,没有化脓,甚至疤痕看起来也不会太明显——这对于这个时代的医疗条件来说,已经是极好的结果。
陈卫国用李婶送来的温水小心清洗伤口周围的皮肤。水是山泉水,清冽甘甜,装在粗陶罐里。他找到一块相对干净的旧布,蘸水擦拭,动作轻柔而专业。
前世的医学训练让他的手法精准——清创要从中心向外画圈,避免二次污染;擦拭要单向,不要来回摩擦;保持干燥,有利于痂皮自然脱落。
做完这些,他把用过的布条扔进灶膛。那里已经积了厚厚的草木灰,是前几日李婶帮他生火煮水时留下的。
今天该去拿祠堂的钥匙了。
陈卫国换上那件补丁较少的蓝色上衣,戴上旧军帽——帽子能遮住额头的伤疤。他拿起木棍,推开门。
五月底的阳光已经很有些热力。青山坳的早稻已经插完,田里一片新绿。远处的山坡上,有人在给玉米地除草,弯腰的身影在绿色背景上缓慢移动。
生产队今天没敲上工钟。陈卫国从记忆碎片里知道,插秧结束后通常有两三天的“小歇”,让村民们处理自家自留地里的活儿,或者上山砍柴、采药。
村道上人比平时多些。几个妇女坐在屋檐下纳鞋底,一边说着家长里短。看见陈卫国,她们停下话头,笑着打招呼。
“傻根出门啦?”
“头好了?”
“看着精神多了。”
陈卫国点点头,算是回应,脚步不停。
老支书家住在村子中央,是一栋三间的青砖瓦房,在清一色的土坯房中显得很醒目。院墙是用碎石垒的,不高,能看见里面的菜畦和鸡舍。
院门开着。陈卫国走进去,看见老支书陈大山正坐在屋檐下的竹椅上,手里拿着张报纸,戴着老花镜在看。
“支书。”陈卫国在院中站定,喊了一声。
陈大山抬起头,从眼镜上方看他:“卫国啊,进来坐。”
陈卫国走过去,在旁边的矮凳上坐下。这是原主的习惯——不坐椅子,坐矮凳,以示恭敬。
“头好了?”陈大山放下报纸,仔细打量他的额头。
“好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陈大山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,摸索着解下一把黄铜的、已经磨得发亮的旧钥匙,“祠堂的钥匙,初一祭祖,你二十八、二十九两天去打扫,三十我检查。”
“嗯。”陈卫国接过钥匙。钥匙很沉,上面有简单的花纹,柄上拴着根红绳,已经褪色发白。
“打扫仔细点。”陈大山又说了一遍,“尤其是正厅,牌位要擦干净,但不能动位置。院子里的杂草要除净,屋角的蜘蛛网要扫掉。县里可能有人来,不能丢咱们青山坳的脸。”
“县里……啥人来?”陈卫国试探着问。
陈大山看了他一眼,似乎有些意外傻根会问这个,但还是回答:“公社通知的,说县革委会农业组要下来检查‘农业学大寨’成果,可能要挑几个典型村看看。咱们村的祠堂是民国初年建的,保存还算完好,公社就报上去了。”
他顿了顿,压低声音:“其实啊,我估摸着,是县里想看看各村还有没有‘四旧’没清理干净。不过咱们祠堂早几年就把牌位收起来了,现在摆的是革命烈士名录,不怕查。”
信息在陈卫国脑中迅速整合。1976年,“文革”还没完全结束,但已经接近尾声。基层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度很高,老支书这番话,透露出谨慎和微妙的态度。
“哦。”陈卫国做出似懂非懂的表情。
“你去吧,好好干。”陈大山挥挥手,重新拿起报纸。
陈卫国站起来,往外走。到院门口时,听见老支书在背后又说了一句:“打扫完了,来我这里领两斤米,算工分。”
工分。陈卫国脚步微顿。这是集体所有制下唯一的“货币”。原主作为守村人,每年有固定的“基本口粮”,但额外的工分可以换更多粮食或日用品。
“好。”他应了一声,走出院子。
钥匙在手里沉甸甸的。红绳磨着掌心,有些粗糙。
他没有立刻去祠堂,而是先回了自己的土屋。从柜子里翻出一块破布,一个缺了口的瓦盆,一根用草绳绑着的短扫帚——这些是原主打扫祠堂的工具。
他把工具放在桌上,坐下,开始思考。
县里来人,检查祠堂。这是一个观察外部世界的机会。虽然“傻子”的身份让他无法直接参与接待,但他可以在现场,可以听到谈话,可以观察来人的衣着、言谈、关注点。
更重要的是,祠堂本身。
记忆碎片里,原主每年都要打扫几次祠堂,对里面的布局很熟悉。正厅、侧室、院子、后院。牌位(现在是烈士名录)的摆放。墙壁上的字画(应该已经换成革命标语)。屋梁的结构。地砖的材质。
作为一个有着工程学和材料学背景的人,陈卫国对建筑本身有着天然的兴趣。而且,祠堂通常是村里保存最完好的建筑,可能隐藏着一些信息——关于这个村子的历史,关于建筑工艺,甚至关于地理位置。
他把工具装进破竹筐,挎在肩上,再次出门。
祠堂在村子最东头,靠近山脚,周围没有其他房屋,显得孤零零的。建筑是典型的南方宗祠风格:青砖灰瓦,马头墙,正门上方有石雕匾额,但字迹已经被凿掉,隐约能看出“陈氏宗祠”的轮廓。
门前有三级石阶,石缝里长满了青苔。两扇厚重的木门紧闭,门环是铜的,已经生了绿锈。
陈卫国掏出钥匙,插入锁孔。锁是老式的挂锁,黄铜质地,转动时发出涩滞的咔嗒声。
门开了。
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——灰尘、霉味、还有木头在封闭空间里特有的气味。光线从高高的窗棂透进来,在空气中形成光柱,能看见无数尘埃在其中飞舞。
陈卫国跨过门槛,放下竹筐。
祠堂内部比从外面看更宽敞。正厅大约有五十平米,地面铺着青石板,已经磨得光滑。正对着门的是一面墙,现在挂着一幅毛泽东画像,下面是一张长条桌,桌上摆着几个木牌——应该就是“革命烈士名录”。
两侧墙壁上贴着红纸标语: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工业学大庆”、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。字是毛笔写的,墨迹已经有些褪色。
屋梁很高,是粗大的杉木,榫卯结构。陈卫国抬头仔细看,发现梁上有彩绘的痕迹,但大部分已经被白灰覆盖,只隐约露出些图案边缘——可能是传统的吉祥纹样,在“破四旧”时被抹掉了。
他放下扫帚,先查看整体情况。
灰尘很厚,脚踩在青石板上会留下清晰的脚印。墙角有蜘蛛网,屋檐下有燕子窝——空的,这个季节燕子还没来。后门通往后院,门半掩着,能看见院子里荒草长到了膝盖高。
陈卫国决定从正厅开始。
他打来水——祠堂后面有一口井,井水清澈。用破布浸湿,拧干,开始擦拭长条桌和烈士名录牌。
木牌一共七个,每个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、生卒年、牺牲地点。陈卫国仔细看了一遍。都是青山坳陈姓的人,牺牲时间从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都有。最后一个牺牲在1953年,朝鲜。
他把名字默默记下。这是这个村子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。
擦拭完牌位和桌子,他开始清扫地面。青石板铺得很平整,接缝严密,显示出不错的工艺水平。扫地时,他发现靠近墙角的一块石板有些松动,踩上去有轻微的晃动。
陈卫国蹲下来,用手摸索。石板大约一尺见方,边缘已经磨损。他试着用力按压一角,石板微微翘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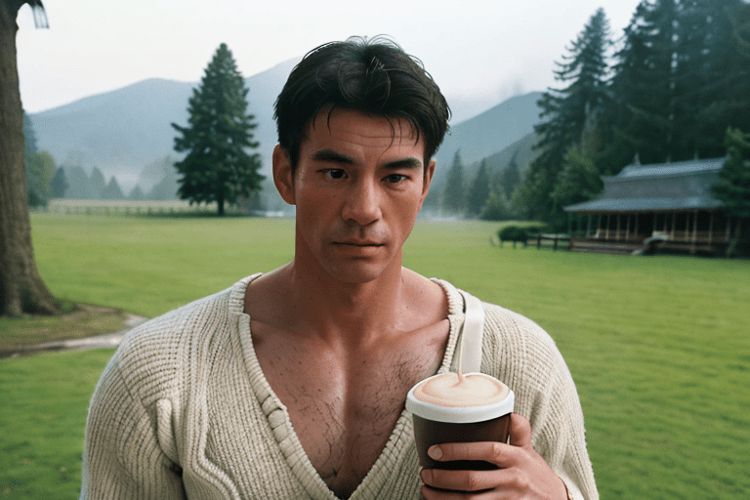
下面有东西。
他心头一动,但没有立刻掀开。先站起身,走到门口看了看外面。村道上空无一人,远处田里有人影,但距离很远。
他关上门,回到石板前。
这次,他小心地掀开石板。石板比想象中重,有二十多斤。掀开后,露出下面的泥土——但泥土是松软的,没有夯实。
陈卫国用手扒开浮土,触到一个硬物。
是一个陶罐,灰黑色,罐口用蜡封着。罐子不大,一只手就能握住。
他拿出陶罐,放在地上,重新盖好石板,把浮土拨回原处,用脚踩实,再撒上些灰尘。
做完这些,他才拿起陶罐,走到窗边的光亮处。
蜡封已经有些干裂,但还算完整。陈卫国用指甲小心地抠开边缘,一点点剥掉蜡。罐口用一块红布塞着,布已经褪色发脆。
他拔出红布,往罐里看。
里面是一卷纸,用细麻绳捆着。还有几块银元,用布包着。
陈卫国先把银元拿出来。一共五块,是民国时期的“袁大头”,保存得很好,边缘的齿纹清晰。银元底下垫着张纸条,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:“祠堂修缮余资,留待后用。民国三十七年,陈氏族长公议。”
民国三十七年,1948年。祠堂最后一次大修的时间。
陈卫国把银元放回罐里,拿出那卷纸。
解开麻绳,纸张展开。是一张族谱的残页,记录了从清同治年间到民国初年的一部分族人名讳。还有一张地契,是祠堂及周围三亩地的产权证明,落款是民国二十五年。
最后是一封信,信纸已经发黄变脆。陈卫国小心展开。
信是用毛笔写的,字迹工整:
“见字如晤。时局动荡,恐有不测。祠中资财已尽数捐于抗战,唯余银元五枚,地契一纸,族谱残页,封存于此。若他日太平,望后人重修祠堂,延续香火。若世道艰难,可变卖以济族人。陈氏第十七代孙,文渊,民国三十七年冬。”
信很短,但信息量很大。
陈卫国沉默地看着这封信。民国三十七年冬,1948年底,解放战争即将胜利,但在这个偏远的南方山村,族人已经预感到时代的巨变,做出了最朴素的安排——留下一点微薄的资财,为祠堂,也为族人。
他把信小心折好,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回陶罐,重新用红布塞住罐口,但没再封蜡。
这些东西不属于他。它们是这个村子的集体记忆和财产。他只是一个守村人,一个意外的发现者。
但发现本身,已经给了他一些启示。
第一,祠堂的建造质量很好,青石板、杉木梁、榫卯结构——说明这个村子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工艺水平。
第二,族人有一定的组织性和预见性。在动荡年代,能做出这样的安排,不容易。
第三,这些物品的隐藏方式——松动石板下的陶罐——可能不止一处。祠堂里或许还有其他“秘密”。
陈卫国把陶罐暂时放在窗台上,继续打扫。
这次他更仔细了。擦拭墙壁时,他留意那些标语覆盖下的痕迹;检查梁柱时,他观察榫卯的工艺;清扫角落时,他注意地面的每一块石板。
又发现了两处轻微松动的石板,但下面都是实土,没有东西。
后院荒草丛生,有一棵老桂花树,树干要两人合抱,树冠如盖。树下有石桌石凳,但已经半埋在土里。院子角落有一间小偏房,门锁着,窗户糊着纸。
陈卫国试着推了推门,锁得很牢。从窗纸破洞往里看,里面堆着些旧农具、破损的桌椅,还有几个木箱。
可能是祠堂的杂物间。
他记下这个信息,继续除草。
除草是个体力活。荒草根深,有些已经长成了小灌木。陈卫国没有合适的工具,只能用双手拔,用脚踩,用木棍撬。
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。五月的阳光透过桂花树的枝叶洒下来,斑斑驳驳。蝉开始鸣叫,一声接一声,嘶哑而悠长。
陈卫国停下来,擦了把汗,看着自己满是泥土和草汁的手。
这双手,前世拿过试管,握过钢笔,敲过键盘,签过亿万合同。现在,它们在拔草,在擦灰,在做最原始的体力劳动。
但他没有感到失落或讽刺。相反,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着他。
劳动本身是有意义的。清理祠堂,让这个承载着村子记忆的建筑恢复整洁,为即将到来的祭祖和检查做准备——这是一件具体、实在、有用的事。
而且,在这个过程中,他了解了这个村子更多。不仅是表面的人口、土地、作物,还有深层次的历史、组织、文化。
了解,是改变的前提。
他继续干活。汗水滴进泥土,手掌磨出了水泡,但他没有停。身体虽然瘦弱,但年轻,有耐力。前世的他注重养生,知道如何调节呼吸,如何分配体力。
中午时分,正厅和后院已经基本清理干净。荒草堆成了几堆,石板路露了出来,石桌石凳也被清理出来。
陈卫国坐在石凳上休息,从竹筐里拿出李婶早上给的饭团——用糙米和红薯捏的,已经凉了,但能充饥。
他慢慢吃着,目光扫过祠堂的每一个角落。
青砖灰瓦,马头墙,高高的屋梁。阳光透过窗棂,在青石板上投下菱形的光斑。空气中弥漫着灰尘、草木和潮湿泥土混合的气味。
安静。只有蝉鸣和自己的呼吸声。
在这个瞬间,陈卫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连接——与这个建筑,与这片土地,与这个时代。
他不是林启明了。他是陈卫国,青山坳的守村人。他要在这里活下去,而且要活得有意义。
饭团吃完,他站起来,继续干活。
下午,他清理了偏房门口的区域,清扫了屋檐下的蜘蛛网,检查了屋顶是否有漏雨的迹象——还好,瓦片基本完好,只有几处需要修补。
太阳西斜时,整个祠堂焕然一新。虽然还是陈旧,但整洁、肃穆,有了应有的庄重感。
陈卫国把工具收进竹筐,拿起窗台上的陶罐,锁上门。
钥匙在锁孔里转动,发出清脆的咔嗒声。
他挎着竹筐,拿着陶罐,往回走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投在村道的黄土上。
路过老支书家时,他停了一下,但没有进去。今天只是初步清理,明天还要来,做更细致的打扫。
回到土屋,他把陶罐藏在床底的角落里,用稻草盖好。这东西不能一直放在祠堂,万一被县里来的人无意中发现,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等检查过后,再找机会放回去,或者……告诉老支书。
但告诉老支书,就需要解释如何发现的。一个傻子,怎么会在打扫时注意到松动的石板?又怎么会想到掀开查看?
陈卫国皱眉。这是个问题。
他决定暂时保管,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晚饭是王老六家送的,一碗稀粥,一碟咸菜,一个煮红薯。王老六的儿子,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送来的,放下碗就跑,似乎有点怕这个“傻根哥”。
陈卫国慢慢吃着,脑中继续思考。
县里来人,大概在六月初八。今天是五月二十八,还有十天。
这十天里,他还能做什么?
除了继续打扫祠堂,保持低调,观察村民,他似乎做不了太多。
但真的做不了吗?
陈卫国放下碗,走到窗边。
暮色渐浓,远处的山峦变成深青色,天空是淡淡的紫红。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,汇聚成一片薄雾,笼罩在村子上空。
蛙鸣开始响起,先是零星的几声,然后连成一片。
这个村庄,这个世界,是如此具体而真实。而他,拥有超越这个时代的知识。
一定有什么,是他可以做的。不用惊天动地,不用改变历史,只是……让某个人过得稍微好一点,让某件事效率稍微高一点。
比如,春梅嫂的小女儿小英,前几天看见她腿上被蚊子咬了很多包,抓得都破皮了。
比如,李婶做豆腐时,点卤全凭经验,有时老有时嫩。
比如,陈老爹的那些草药,如果炮制方法改良一下,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小事。都是小事。
但改变,往往从小事开始。
陈卫国回到床边,躺下。
窗外,最后一线天光消失,黑夜降临。
土屋里没有灯,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星光。
他闭上眼睛,在黑暗中,开始一项前世常做的思维训练:在极端限制条件下,设计最优解决方案。
限制条件:1976年,南方山村,物资匮乏,身份是“傻子”,不能引起怀疑。
目标:在十天內,完成至少一项微小但有效的改善。
可能的切入点:健康、饮食、工具、信息。
健康:预防蚊虫叮咬。可以用哪些本地植物?艾草?薄荷?如何制作简单的驱蚊液?
饮食:豆腐质量不稳定。如何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点卤的关键?温度?浓度?搅拌速度?
工具:清扫祠堂时,扫帚效率低。如何改良?加宽?改变角度?
信息:县里来人时,如何听到更多谈话?假装在附近干活?以送水的名义接近?
一个又一个方案在脑中生成、评估、修改、优化。
星光透过破窗,照在他脸上。
陈卫国的嘴角,极轻微地向上弯了一下。
找到了。
明天,从后山的艾草开始。





![[丈夫把学区房送给保姆,我把他们都扫地出门]全集阅读-胡子阅读](https://image-cdn.iyykj.cn/2408/d656856cb7782d287b0983a7c51cf75c.jpg)
![[青衫错]最新章节列表_[沈知微秦伯]最新章节目录番外+全文-胡子阅读](https://image-cdn.iyykj.cn/2408/1c94d92da8556ece3d51bacb44f49bda.jpg)